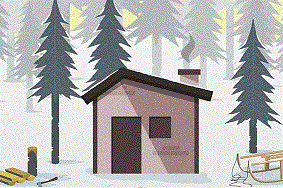饥荒联机版地图怎么生成圈状的,饥荒联机版怎么看地图坐标点
- 百科知识
- 2年前
- 149
- 更新:2022-05-11 11:23:14
饥荒在线地图如何生成圈子?饥荒在线地图怎么看地图坐标格雷厄姆?铺开
【编者按】作为世界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城市之一,描述巴黎的篇章数不胜数。无论是美食、文化、风景、历史、时尚、建筑、名人轶事.不会让人厌烦。还有来自英国的历史学家格雷厄姆?罗伯写的《巴黎,光影流动的盛宴》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独特的巴黎传记。
《巴黎:光影流动的盛宴》 ;格雷厄姆罗布/作者,金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8-31
一月份,我们通过初步采访发现了令人鼓舞的证据。就在好莱坞音像店和欲望都市俱乐部的对面,圣德尼教堂外的道路同时向南北倾斜。南侧是古罗马大道和圣德尼郊区公路,交汇处就是现在的多莫伊斯站。北侧的路是缓坡,通往下面的圣但尼平原。在中世纪,这里曾经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再往下是一片沼泽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卢特西亚平原是神圣的“高卢中心”。根据凯撒在《高卢战记》年的记载,当时的德鲁伊教徒从地中海和不列颠尼亚远道而来,就是为了在“高卢中心”选举他们的大祭司。
避难所村仍然有交通要道的噪音。汽车和卡车双向通行,络绎不绝。与拥有精致城区的巴黎相比,拥挤的人群和简陋的店铺让圣礼拜堂村更像一个大城市的烟火。圣德尼教堂的对面是牧师巷。走到尽头,可以看到圣心教堂的铁栏杆,俯瞰围墙。下面像蚁丘一样的山坡上,家家户户密密麻麻的屋顶和烟囱。来自亚眠、里尔佛兰德斯和英吉利海峡的列车摇摇晃晃地穿过深谷,驶向前方的巴黎北站。
从高地看圣德尼教堂
人们在黑暗的圣德尼教堂窃窃私语。教会提供的小册子(“欢迎和传递友谊”)简单介绍了教区的历史,说它是以埋葬向卢特西亚介绍基督教的圣德尼(连同他的斩首)而命名的。公元475年,来自南泰尔的修女圣热纳维尔傅(Saint Genevier Fu)提议为圣德尼建造一座神龛,以便找到未来的圣德尼教堂。圣热内维尔傅不仅善于组织反对匈奴的运动,缓解人民的饥荒,而且知道为了传播圣德尼的名声,应该把像他这样的烈士埋在每个旅行者必经的关隘里。
另外,圣德尼礼拜堂隔壁是圣女贞德殿,小册子上写着:1429年,解决了奥尔良之围的圣女贞德在圣德尼礼拜堂祈祷了一夜(还有一种说法是圣女贞德因为腿上有箭伤,要在教堂再待一夜),然后骑着她的马和鞭子,冲向英军占领的巴黎城门。为了感谢圣女贞德保卫巴黎的安全,人们在圣德尼教堂旁边的空地上修建了圣女贞德庙。我们继续在烛光下翻阅小册子,结果在第二页的上方,我们读到了下面这句话:“(圣德尼礼拜)教堂前的主要道路是在高卢-罗马时期竖立起来的。这条路延伸到圣德尼镇及其周边地区,穿过蒙马特和梅内蒙当之间的山口,通向塞纳河上的黛丝岛。”
在教堂里
我不是第一个发现圣礼拜堂的人。当然,让人们“抢先一步”让我略感失望,但与找到第一个确凿证据的喜悦相比,我的沮丧不算什么。所以三个月后,玛格丽特和我第一次乘坐旅行车。
爬上了巴黎唯一的一个关口(用脚踏轮子)。我们在圣礼拜堂门前转弯,和一群行人、司机一起爬上南坡。为了纪念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当我到达坡顶时,我转过头,回头看了看圣德尼教堂。不幸的是,一辆搬家公司的卡车刚好经过,挡住了我的视线。不仅如此,我还被巨大的车身挤压,差点摔倒在脚下。卡车轮胎和路边石之间只有一条狭窄的沥青路面。我不得不暂时离开圣德尼教堂,专心骑车,以免一不小心毁了自己的生活。我们的探险到此结束,我连一个像样的纪念碑都拿不到(“我在穿越圣礼拜堂山口时不幸死去”)。太可惜了!
“公路工人通行证(Val River):是为了宣传目的而设立的,缺乏实证。违反第11条。”
“骑行者关(萨瓦省):地形不详,由当地骑友编造。违反第11条。”
说到这里,100 Pass俱乐部对我“发现”的Pass并不陌生。事实上,该俱乐部的一名成员在参观巴黎圣母院的地下考古墓室时,注意到了一张古巴黎浮雕纸质地图上的“圣礼拜堂通道”字样,并将结果报告给了该俱乐部。白艾委专家对此进行了讨论,最终认定证据不足,不予采信。100 Pass俱乐部的主席回复我的电子邮件,就像一名自行车手在赛车比赛中绕过地上的一个洞一样迅速而直截了当:“Pass从未得到官方认证。它从未在巴黎的其他地图上显示过,也没有被一个道路纪念碑命名过。”
但至少主席的话给我们留下了一丝希望:“关隘……”他没有明确否认圣礼拜堂关隘的存在。因此,从逻辑上讲,我们下一步应该做的是在地图和路标上标出“关隘”。
于是我先给法国国家地理研究所发了一封邮件,然后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出了圣礼拜堂山口的具体坐标和可以作为证据的补充材料。根据我在图书馆收集的资料,在伦巴多总督和奥斯曼男爵用挂满煤气灯的林荫大道取代巴黎黑暗小巷的时代,一位名叫西奥多瓦克尔的考古学家像“一只一直蜷缩着的刺猬”一样在巴黎的废墟中搜寻,试图拼凑出卢特西亚的古老影像。好事多磨。这个瓦克尔发现了索福乐路下的前罗马广场,以及加斯帕尔蒙日路附近的卢特西亚竞技场遗址。瓦克尔不是作家,而是个白痴。
对考古发掘着迷的学者;然而,在他去世十多年后的1912年,一位地理学家从瓦克尔生前所做的大量笔记和草图中有了惊人的发现,首次向世人揭示了“圣礼拜堂山口”的存在。此后,许多地理学家(但不是制图师)进行了实地考察,试图理清巴黎日益混乱的过去。他们穿过了自前寒武纪以来就存在的河床和静止带。
着古老海水潮气的山丘,在著作中不约而同提到了坐落于史前“锡之路”上的圣礼拜堂隘口。好几周过去了。要么是地理学院派往圣礼拜堂隘口的考察队从万塞讷森林出发,再也没能回来,要么是我的信在被拆阅后让人直接扔进了废纸篓。我在等待地理学院回复的同时,为了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给巴黎第十八区的区长和市政厅的官员也写了信。一个月后,地理学院的回信寄到了。信中说巴黎的这个隘口“从
地理和地形意义上讲”确实存在,是“蒙马特和肖蒙山丘之间的最低点”。但是,写信人又不无揶揄地表示,这个隘口“迄今为止”都没能出现在地理学院的地图上,原因有二:其一,“该地区的城市空间结
构非常密集”;其二,“当地居民目前并未使用‘圣礼拜堂隘口’这一称谓”。换言之,那一片区域的地图上已经标注了太多的地名,而如果一个探险家来到圣礼拜堂村,问那里的人:“往圣礼拜堂隘口要怎
么走?”肯定会看到对方一脸茫然(除非他碰巧问到的是个地理学家,又或者是撰写了圣礼拜堂教区历史的那个人)。
我徒劳地等待着市政官员的答复,我本以为比起地理学院的审慎,市政官员会更坦率、更接地气一点。但事到如今,他们会不会回复我似乎已不再重要。就算圣礼拜堂隘口能够得到承认,政府命人在路边为它镶一块镀锌的标记,也不过是让巴黎多一个来自遥远过去的路障,不过是给自行车手多留一处拍照纪念的地方,不过是替这座城市多添一幅能稍稍持久些的涂鸦前提是在路旁遍布着的、口吻严峻的交通标志(“禁止通行”“旅游区已达尽头”“你没有道路优先权”等等)以外还能为圣礼拜堂隘口的路碑找到空间的话。
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人类建造起来的城市从来都对人类的欲望无动于衷。一座城市以坚实的形态向人展示由他们所虚构出来的历史,它折射人的亲密,讲述人的荣耀、爱情、永恒的骄傲、只有一人知晓或需代代笃信的传奇。它足以让最狂妄的赢家也低下头来,懂得自己的梦其实有多渺小。巴黎从蒙帕纳斯大楼的观景台上露出了真面目,入夜后总有警卫在那儿巡逻,以防想轻生的市民自楼顶一跃而下。大楼的照明彻夜不熄,但在闪烁着的灯光照不到的地平线上,泰半皆是黑暗。
活生生的城市也是大大的坟场,是一座携带着万千人口、不断下沉的山,死者终归入土,生者尚要奋力攀登。国王、王后和皇帝不过是城市的仆人。他们相帮擦除城市的痕迹,抹去一切记忆的可能。拿破仑三世(奥斯曼男爵)对巴黎的大改造湮没了千万平米之上的历史,以某一场战役命名的林荫道消除了百万人共有的回忆。在拿破仑三世的统治结束之时,国家档案馆的珍贵史料让巴黎公社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而两个世纪以前,在距离巴黎八千公里的南大西洋的小岛上,被流放了的拿破仑·波拿巴正感叹他终未能成的雄图霸业:“只得二十多年,又哪里够用。”在他看来,千里之外、目力所不能及的巴黎曾是他把玩于指间的一颗宝珠。如果上天能再给他一点时间,旧城巴黎便会彻底消失:“你寻找亦是徒劳,它连半点痕迹都不会留下。”(《圣赫勒拿岛回忆录》)
中尉并没有犹豫“就像你能想象的那样,我连忙照做了。”
1792年的拿破仑,当时他还是一名23岁的中尉。
他继续朝卡鲁索广场走去,进了一个朋友的家。这幢房子已经成了仓库,里头堆满匆忙逃走的法兰西贵族的财物,而小件的家具、装饰品以及全家福都送到当铺换成了真金白银,让贵族们随身带走了。
中尉走上二楼,穿过东倒西歪、被这个世界抛下了的各类家什,看向窗外:暴民如潮水一般涌进杜伊勒里宫,无情屠杀了充当守卫的瑞士近卫队的队员。就像是在剧院的楼座看一出荒诞的大戏一样,中尉从那扇窗户的后面目睹了法国君主制的暂时终结。多年以后,当初的炮兵中尉已然成了皇帝,他微服出巡,徘徊在巴黎的街头,试图偷听人们谈话的内容,试图揣摩人们脸上的表情,以判定他所创造的新世界是否如他所愿。他当然也试图寻找卡鲁索广场边那幢铭刻了太多记忆的房子。只可惜他所下达的翻新街道的命令得以迅速执行,“那一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再也找不到当年的那幢房子了。”
今天的卡鲁索广场
圣礼拜堂隘口依然没有标记在地图上,巴黎也依然没有山。和人类不一样,这样的地理事件本身无需纪念,或许正如国家地理学院在信中暗示的那样,对巴黎来说,圣礼拜堂隘口已经不复存在。十九世纪的时候,途经这里的铁路几乎把隘口完全轧平了。铁路也改变了隘口的景致,火车头喷出的白色蒸汽描摹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为人们的想象力提供了全新的舞台:看哪,在我们脚下的岂不是一条条人行道,岂不是一座座烟囱造就的宫殿,岂不是行进在黑色运河上的一列列幽灵般的队伍!
到2010年,圣礼拜堂隘口的重要性也只有通过交通流量来体现了。它是这座未来之城的脑干,甚至在巴黎西族还没有定居塞纳河上的小岛之前,就已经有旅人从此通过了。现在,它是自伦敦始发的欧洲之星的必经路线。如果你当真好奇圣礼拜堂隘口究竟在什么地方,不妨从欧洲之星的车厢左侧往外看,在经过标有“平原集市”(昔日神圣的“高卢中心”)字样的车棚后不久,火车便来到了已然被人忘却的圣礼拜堂隘口。因为刚巧爬过坡顶,你会隐约注意到发动机一收一放、火车车轮受到牵引而后忽然松弛的感觉。但是这个隘口实在很容易错过,因为还没等你回过神来,车厢里就已经响起了广播:“尊敬的乘客,我们将在几分钟后到达巴黎北站。”是时候合起书本、取下行李,走进神奇的巴黎了。在那里,即使是最安静的街道也充满了令人着迷的探险故事。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