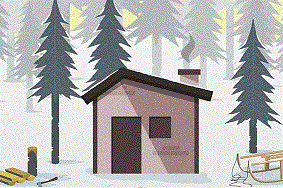adele阿黛勒(阿黛勒人物分析)
- 百科知识
- 3年前
- 181
- 更新:2021-12-20 09:39:56
【编者按】埃琳娜费兰特是目前最受欢迎、最神秘的意大利作家。Elena ferrante是笔名,她的真实身份已经很久没有人知道了。直到今年,媒体才通过不懈的追踪发现了她的真实身份。从2011年到2014年,Elena ferrante发布了《我的天才女友》 《新名字的故事》 《离开的,留下的》 《失踪的孩子》和《我的天才女友》,并且每年都有频率。这四部与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的翻译版本在欧美很受欢迎。首批《纽约书评》中文版《那不勒斯四部曲》已由99位学者引进出版。
在史诗结构中,四部曲描述了出生在那不勒斯半个世纪的两个女孩(埃琳娜和莉拉)之间的友谊。以下是2014年12月《新名字的故事》本书的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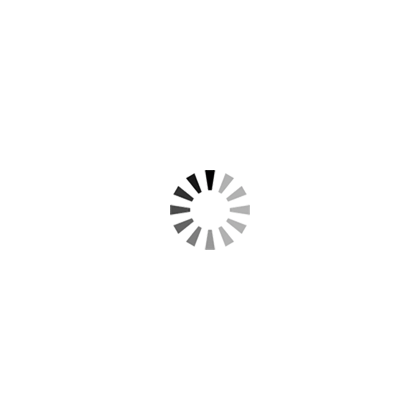 在费兰特名作《那不勒斯系列》的第二本书《尤利西斯》中,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对话:莉拉在街上遇到了她的前老师奥利维耶罗。令老师沮丧的是,尽管莉拉很有天赋,但她已经快20岁了,从小学开始就中断了学业。她已婚,有一个小儿子。奥利维耶罗老师没有理会小男孩雷诺,只注意到莉拉拿着的一本书。莉拉非常紧张。
在费兰特名作《那不勒斯系列》的第二本书《尤利西斯》中,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对话:莉拉在街上遇到了她的前老师奥利维耶罗。令老师沮丧的是,尽管莉拉很有天赋,但她已经快20岁了,从小学开始就中断了学业。她已婚,有一个小儿子。奥利维耶罗老师没有理会小男孩雷诺,只注意到莉拉拿着的一本书。莉拉非常紧张。
“这本书是《奥德赛》。”她说。
“你说的是《尤利西斯》英里?”问问老师。
“不,是关于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多庸俗。”
“然后呢?”
“仅此而已。我们的脑子里充满了愚蠢的事情。我们是由骨头和血肉组成的。大家都差不多。我们只想吃、喝、做。”
奥利维耶罗骂莉拉低俗出口,然后告诉她,每个人都可以成家,但她应该做点大事。“不要读你看不懂的书。对你没有好处,只有坏处。”老师说。
“有很多东西是有害的。”莉拉说。
这段简短的对话尖锐地指出了这些非凡的作品,以及其作者——最具影响力和神秘的意大利作家——的最重要部分。Ferrante ——,隐藏在笔名后面,从不公开露面,从来不隐藏这样的事实。像——和《我的天才女友》一样,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就其自身的方式、愿景和野心而言,是一部史诗。这些书的叙述者分别是—— 《新名字的故事》 (2011)、《离开的,留下的》 (2012)、《失踪的孩子》 (2014)——。
她的旅程不在海上,她的旅程更内化。在这部贯穿童年、少女时代、青年时代和母亲时代漫长下午的那不勒斯“成长小说”中,它逐渐被揭示出来。这部小说和19世纪的小说一样,人物复杂,情节次要,但故事的核心是二战后在破败的那不勒斯郊区长大的埃琳娜和拉法利亚塞罗(别人叫她“丽娜”,只有埃琳娜叫她“莉拉”)之间的友谊和战争。
这部小说贯穿了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飞跃和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动荡,直到今天。莉拉和埃琳娜在彼此眼中交替成为“天才朋友”。他们不可避免地密切参与他们的生活。几十年来,它们相互重叠,相互发散。
故事开始于2010年,当时莉拉成年的儿子雷诺打电话给埃琳娜,说66岁的莉拉已经失踪。埃琳娜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她开始回忆自己在那不勒斯的青春。——埃琳娜的父亲是门房,母亲是家庭主妇,和鞋匠的女儿莉拉成了最好的朋友,在他们的娃娃掉进人人害怕和放高利贷的唐阿切尔家阴暗的地窖后,她再也没有背弃过我们。
然后我们随着时间前进,婚姻,孩子,婚外情,离婚,成功或惨败,死亡,谋杀,文学成就。书中的人物,就像古代故事中的人物一样,在他们从出生开始设定的命运和他们控制自己命运的努力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谈判。
故事从意大利宿命论的中心那不勒斯——和黑社会组织卡莫拉的大本营——开始,卡莫拉像雾一样笼罩着每一本书,也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要面对和处理的“社会原则”。“我一点也不怀念我们的童年。”莉娜在四部曲的第一本《我的天才女友》开头说,“因为我们的童年充满了暴力。”)
虽然莉拉对《尤利西斯》的解释不着边际,但她的回答却准确得让人无法忍受,关键不在于文字或文学上的解读和误解。老师可能不知道Joyce是谁,但正是她发现了莉拉和Elena身上的天赋,鼓励他们通过学习获得独立,逃离悲惨的环境,将来过上囚禁的生活。费兰特的那不勒斯系列本质上是一部关于知识的小说——关于知识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知识,性知识,政治知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需要什么样的知识?我们如何获得这些知识?我们所拥有的知识如何改变我们,伤害我们,同时让我们变得更强大?我们想知道而宁愿永远不知道的是什么?我们能控制什么,什么在控制我们的生活?
在《我的天才女友》中,很明显,莉拉、埃琳娜和那不勒斯的其他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不同寻常地意识到了权力结构。他们知道该尊重谁,输给谁,即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有能力赢。在小学教室上演的一幕中,莉拉——因为她的聪明才智和对那些她应该示弱的人的蔑视而受到大家的尊敬。恩佐,一个卖水果的女人的儿子,参加了一场数学竞赛。这个男孩几乎不会说标准的意大利语,但他是在脑子里想出来的。
了复杂的计算后,用那不勒斯方言说出了答案,身为班级明星的莉拉战胜了恩佐。“从那时开始,莉拉就表现出一些很难描述的态度,”埃莱娜说,“比如说,我清楚地看到: 莉拉可以自己控制才能的使用。”很多年后,当恩佐开始清算自己的命运和这个世界时,他将成为莉拉的拯救者。但那场数学竞赛后,男孩子们因为莉拉打败了恩佐而讨厌她,开始朝她和埃莱娜身上扔石头——一种同时涵盖了愤怒和尊敬的暴力。
几年后,仍在她们的童年,莉拉为了捍卫遭受街区的男孩子们嘲弄的埃莱娜,用一把裁皮刀顶住马尔切洛·索拉拉的喉咙——后者是当地一个克莫拉黑帮成员的儿子,并且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她随时准备好动刀。这吓坏了马尔切洛,却也激起了他终生对她的爱。这,同样也是费兰特的风格——去追溯暴力和爱之间那几乎无法察觉的界限。
这些故事带着血迹、谋杀、经血,同样还有泪水和汗水。男人们对女人暴力相向,女人们亦以暴力还击。女人们被背叛,同样也在背叛——自己和他人。费兰特所有的作品中,都有很多赤裸裸的、通常来说毫不浪漫的性爱。将这些作品归为“女权主义”作品是准确的,虽然这也许是一种简化。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些作品探索身为女人的完整经历中那些私密的、甚至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细节,以及在那不勒斯系列中,探索女性友谊的深刻复杂性时所带有的审视和强度,是当代文学——可以说是任何时代的文学——少有的。此外,那不勒斯系列出色、持续地探讨了嫉妒——这种最为致命的情感,因它有时候将自己伪装成爱。
以《新名字的故事》中的这段为例,这本书的开头,是16 岁的莉拉和堂·阿奇勒的儿子斯特凡诺·卡拉奇的婚礼。随着婚礼的进行,莉拉意识到她不爱斯特凡诺,永远也不会,她突然明白,他并非完全自由的,他和这个街区的所有人一样——她相信自己不会——受制于索拉拉一家,在婚礼上那家人不请自来,在表面上看似优雅的礼节后面,是 暴力的恐吓。
作为一个笨拙的少女,埃莱娜非常嫉妒自己的好朋友即将进入性爱世界。在婚礼的那天早晨,有一场类似于部落仪式的瞬间,埃莱娜为莉拉洗澡。
这个场景具有典型的费兰特风格——带着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动;生活在展开的同时也在被记录,女性叙述者挣扎着理清自己矛盾而混乱的内心冲突,然后带着一种令人戒备全无的诚实,将自己无从逃脱的念头和盘托出。
埃莱娜帮助莉拉步入成人世界,但却是莉拉刺激埃莱娜产生了一种竞争意识——无论是性爱,还是文学——这也激励了她的自我反思,并在后来让她成为了一名小说家;这种竞争意识同样驱使她渴望在婚前失掉自己的处子之身,这在1950 年代的那不勒斯不啻于一种挑衅和叛逆。(那个夺走她处子之身的男人日后会写评论表达对她的处女作的不屑一顾。)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两个好朋友的生活会是彼此的一面黑色的镜子。在她父亲不允许她参加升中学的考试后,莉拉辍学,抛弃了自己在学业上的野心。她成了一个修鞋匠,后来成了一个耀眼的、迷人的新娘。再后来,她干过一系列卑微的工作,包括在一个肉食厂打工,那里糟糕的环境让她的身体备受折磨。
埃莱娜从文科中学顺利地毕业,这是她通向上层中产阶级的第一步。莉拉尽管辍学了,但她还是学习更好的那个,她还帮助埃莱娜补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埃莱娜成功考进了很有威望的比萨高等师范学院,嫁给了一个古典学者,开始写一些文章,也令她自己惊讶的是,她最后写出了一部小说,(“每一页里都回荡着一种有力的东西,我不明白这种力量来自哪里。”她的小说的编辑告诉她。)
我们会发现,莉拉一直也在秘密地记笔记。在《新名字的故事》中,她将这些笔记本托付给埃莱娜保管。后来,在这四部曲最令人心碎的一个场景中,埃莱娜将这些笔记本都推进了阿诺河里——一种近乎谋杀的举动,但埃莱娜觉得自己必须如此,以便向她的天才朋友宣示自己的权力。
尽管如此,埃莱娜内心一直对莉拉抱有某种敬畏,因为莉拉拥有真实的感情,“能够打破陈规旧矩”,去主动获取她想要的东西;而埃莱娜觉得自己“总是落在后面,总是在等待”。后来,埃莱娜意识到使自己成名的小说,其实是从莉拉小学时写的《蓝色仙女》中汲取了强大的情感力量——奥利耶维罗老师曾经对那个故事不屑一顾。后来,埃莱娜将写有《蓝色仙女》的那些笔记带给在肉食厂工作的莉拉,莉拉将它们投进火里一把烧了。
在《离开的,留下的》中,埃莱娜的小说因其具有的“现代力量”获了一个文学奖。那是1969 年。一颗炸弹在米兰喷泉广场的国家农业银行爆炸,导致17 人身亡,几十人受伤,这也是意大利“沉重年代”中一个最神秘的插曲。在她的获奖感言中,埃莱娜说自己和“走在月亮的白色旷野上的宇航员”一样开心。她给身在那不勒斯的莉拉打电话,告诉她自己获奖的事。莉拉早已经从当地的报纸得知了这一消息,并揶揄了她的措辞:
“月亮的白色旷野,她语带讽刺地说,有时候什么都不说总比说些无意义的废话好。然后她说,月亮只是几十亿块石头中的一个,就这些石头而言,你最好把双脚稳稳踩在地球上的这堆混乱中。”
很快,埃莱娜生了一个女儿。“我经历了可怕的疼痛,但那没有持续很久。当宝宝出来时,我看到她了,黑头发,一团紫色的生物,充满能量,在扭动在嚎哭。我感到一种生理快感,如此强烈,没有其他任何快乐可以比拟。”费兰特写道。埃莱娜给莉拉打电话,“这种体验真美好,”她告诉莉拉。
“什么?”“怀孕,生产。阿黛尔很漂亮,很美好。”
莉拉回答:“我们每个人都按自己想要的样子叙述自己的生活。”
让我们回到作者的问题上来。费兰特是个笔名,她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从没有人见过她,这让她在过度迷恋形象——如果你不出现在电视上,你就几乎不存在——的意大利有了一种奇怪的角色。
在意大利,她的出版人是很小的E/O 出版社,她作品的英文版是E/O 的姊妹出版社Europa 出版的,这两家出版社都以出版翻译作品见长。2013 年,詹姆斯·伍德在《纽约客》上为《我的天才女友》写了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评论后,费兰特开始收获了很多忠诚的英语读者——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她的英语译者安·戈德斯坦(Ann Goldstein)极度生动而流畅的英语译本。她的匿名状态助长了很多流言蜚语。她的作品是否是一组作家的共同作品?她是不是电影圈的人?(那不勒斯系列第三本《离开的、留下的》中那些粗糙暴力的段落,比前两本都更政治性,场设置在“沉重年代”和当时方兴未艾的女权主义运动,有时给人剧本的感觉。)
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她到底是不是个男人?——相比于费兰特的作品,这个问题更多地反映了今日意大利的状况。正如一些人暗示的,她是否可能是那不勒斯作家戴蒙尼科·斯塔尔诺内?她是否就是安妮塔·拉娅——她是E/O 出版社的顾问,曾将克里斯塔·沃尔夫等人的作品从德语译成意大利语,且恰好是斯塔尔诺内的妻子。去年9 月,在《金融时报》刊登的一份问答文章——这是她少有的公共交流——中,费兰特承认她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当被问到如果她必须要放弃写作,她如何谋生时,她答道:“靠这些年里我每天在做的工作——并非写作。”她还将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艾尔莎·莫兰黛引为对她在文学上影响最大的人。
很多年来,费兰特的笔名犹如某种证人保护程序那样运作着。信息的缺失会滋长怀疑。费兰特是否和莉拉和埃莱娜一样卷入婚外情?她是否像《被遗弃的日子》里的奥尔加那样,在丈夫为了另一个女人抛下她之后,她、陷入一种抑郁的疯狂?
又或者,她就像《遗失的女儿》中那个离异的叙述者、非常痛苦的年轻母亲勒达,因为一种窒息感,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女儿? 她是否和《被遗弃的日子》《遗失的女儿》,还有那不勒斯系列中的埃莱娜那样,一边周旋于应对为人妻母所要面对的那些支离破碎的日常生活的需求,一边急切地想要清理自己的精神空间,找到精神的平静以便可以写作?她是否和那不勒斯系列中的埃莱娜一样,出生于那不勒斯的贫困的社区,父母几乎大字不识,后来通过学习主宰了自己的命运,但一直恐惧自己被拉回她以为自己已经逃离的世界、变成更原始的那个她,那个说着那不勒斯方言而非意大利语的自己?谁离开了,又是谁留下了?
费兰特所有的作品——尤其是那不勒斯系列,可以被视作当代的《变形记》。她所有的作品中最重要的“变形”,是那些处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女人们。女儿变成了妻子,然后又变成了母亲,但她们身上始终保留着这三种角色,这些不同的角色在她体内一直在争执,在冲突。在《被遗弃的日子》中,奥尔加的孩子们让她“为那些我没有犯下那些黑暗、虚构出来的罪孽赎罪”。在《讨厌的爱》中,故事寓意更加黑暗,主人公迪莉娅也是一个未婚的漫画家,穿着她刚去世的母亲在溺水前穿的浴袍,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她的母亲。在一处让人不安的性爱场景中,并非出于完全的自愿(但也算不上侵犯),迪莉娅和她母亲的情人的儿子上床了。
在《遗失的女儿》中,抛下丈夫和两个女儿的勒达在度假,她发现自己对海滩上的来自那不勒斯的一家人很感兴趣。那个蹒跚学步的女儿——名字碰巧也是埃莱娜——丢失了自己的布娃娃;勒达将玩偶捡起来,出于她自己都不清楚的某种神秘心理,将那只玩偶紧紧抓在自己手里。甚至她笔下的那些名字也会转化成另一个。这些现代的、非正统的女主人公创造、再创造了她们自身,改变了自身的形状,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从痛苦变得平静,又经常再度回归痛苦。与过去那些世纪里的文学女主人公们不同,费兰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能够奢侈地在现代世界行动——带着所有的怀疑和不确定性,更多地是回应自身混乱痛苦的意识,而非在战后意大利已经消失的那些沉重的社会束缚。
《被遗弃的日子》是关于奥尔加的故事,这个38 岁的女人彻底被她丈夫抛弃她的事实摧毁了,但事实上,经过一段时间她又重建了自己,她从外部审视自己,就好像在观察他人。这些女人可能是生活里的受害者,但是她们用一种只有自己清楚的方式主掌了自己的命运:通过一种极度近距离的观察——这种观察是一种意志的行为,但经常缺乏决心和启示。在《被遗弃的日子》最后,奥尔加向一个和她有暧昧关系的男人解释自己在些疯狂的日子经历了什么。“我的反应过度了,刺穿了事物的表面。”她说。“然后呢?”她的同伴说。“我跌倒了。”“你最后在什么地方结束了?”“无果。那里既没有深渊,也没有悬崖,什么都没有。”
在《离开的,留下的》的结尾,埃莱娜在完成一本新书,她不确定那会是一本小说还是别的什么。当被问到作品的主题时,她回答道:“男人捏造了女人,”然后交谈变成了皮格马利翁和类似的故事。但是,在意大利版的原文中,这句话更加微妙、暧昧。埃莱娜的回答是“男人们捏造了女人”——同时也可以指代“女人们捏造的男人”。至少,自从但丁的《地狱篇》以来,fabbricare——去“捏造,制造、锻造”,这个词自身就暗含了伪造和诡计的意味。我们每个人都按自己想要的样子叙述自己的生活。
虽然她的故事背景都设置在意大利,但费兰特的书中并没有什么优美的风景。故事发生在那不勒斯丑陋憔悴的郊区或那些毫无特色的公寓里;偶尔,故事场景变成一片浪花泼溅的海滩抑或是中上层知识分子们那些考究华丽的公寓。《我的天才女友》中,有一处令人难忘的场景——在莉拉和埃莱娜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们试着从家里走到海边,她们只是听说、却从未去过海边。对于那不勒斯系列而言,大部分的场景都如古希腊戏剧的设置那样简略,这样反而更容易去窥探人物的内心世界。
费兰特的所有作品都欠缺幽默感。任何一本她的作品都不会让你大笑,除非是那种阴暗的、令人不安的笑。“书籍不会改变你的生活,”费兰特在2014 年9 月对《金融时报》说,“如果它们够好的话,它们至多可能会给你带来伤害和困惑 。”
阅读她的作品也会产生这种累积的效应。她的小说都骇人地会冲向某个如深渊的地方。和很多人一样,我是到很晚的时候才开始阅读费兰特。这一年,第一次阅读她的作品几乎是一种启示。是否有一种可能,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治理意大利的那些年里——那个充斥着广告女郎和未成年少女的意大利,充斥真人秀和整形手术的意大利,有着全欧洲最低的女性就业率的意大利,经济和文化停滞的意大利,那个对变化普遍持麻木和抵制态度的意大利,在这些年里,很多左翼的知识分子住在他们舒适的、继承来的公寓里,心不在焉地探究为何安娜·马格纳尼的那个意大利变成了鲁比·偷心者——是否有可能,自始至终,这个国家都存在一个清晰、可怕的声音,它贯穿了那些历史时刻,同时又超越了它,讲述了意大利女性所有的矛盾和力量?是否有可能,她一直在这里,只要我们关上电视、聆听?
在《离开的,留下的》的结尾,小说的时间是1976 年,我们在猜想已经成为成功作家以及两个孩子的母亲的埃莱娜会发生什么,她已经和钝感的丈夫日渐疏离,却发现自己狂热地爱上了尼诺·萨拉托雷——那个和她在一个街区长大、已经变成知识分子的男孩,尼诺同样也已结婚,在四部曲中那个至关重要的插曲中,他曾是莉拉的情人——事实上,正是他激励了莉拉去阅读《尤利西斯》。
我们仍然不知道,66 岁的莉拉彻底消失之后,她又会彻底经历什么。几年前,她曾经警告埃莱娜不要写她的故事。她会和《讨厌的爱》中的那个母亲阿玛利亚遭遇同样的命运吗——极有可能像是自溺在海里?她是否会像《被遗弃的日子》中的奥尔加一样,获得精神的某种宁静?……对我们这些沉迷于费兰特的世界不能自拔的人,我们会像关心生活中的人和事一样在意这些小说人物的命运,在读完这部令人难忘的系列作品后,我们开始更有力地关照世界和我们自身——我们几乎是迫不及待想读到她最新的作品。
上一篇:怎么样喝红酒(怎么样喝红酒最好)
下一篇:妩媚美女图片(手绘美女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