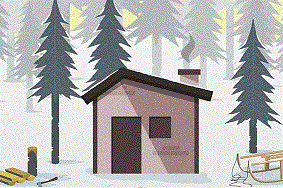723动车事故(723动车事故为什么要掩埋车头)
- 生活妙招
- 2年前
- 97
- 更新:2022-03-27 14:45:31
天空明亮。丁正躺在床上,仿佛听到了墙壁的声音。“温度”是护士的声音。
丁羽西生病反映手机被抓拍,早上6:30。
床上不能有体温计,手指上不能有氧气夹。这是卧室,不是医院病房。他转过身,两个孩子还在睡觉,下巴上还残留着唾液的痕迹。
他们刚刚对这个33岁的男人做了一些治疗。出院半个月了,老婆还在隔离点医学观察,他的疯狂焦虑现在连上了。
丁羽西喘了口气,小心翼翼地帮孩子踢被子,省得自己再睡。起床后,他还要面对邻居和同事。
截至3月24日24333.6万,全国累计报告确诊81218人,死亡3281人,治愈73650人。
他们被解雇了。疑似患者中,确诊患者连续治愈,却发现是“感染者”。
北京大学精神医学研究所2004年的研究所调查显示,3个月内抑郁和焦虑状态的检出率分别为16.4%和10.1%,可能是慢性的。北京的精神病医院和餐饮医院也在2003年末发现,约85%的患者出院后心理健康状况不佳,认为自己很不幸,不会被社会正常接纳。嫉妒。
固化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是,传染病留下了长久的年轮。
离题
这太熟悉了。从医院出来。握手,献花,拍照,医生戴上口罩祝贺,“恭喜你治好了,克服了困难,然后出院”,这两张全脸。“正式而温暖的心”,丁回忆道。
曾是汕头25段临床诊断病例。讨论到2月12日,“免费关注”,丁在朋友圈写道。
到了老板办公室,他马上把医院的信息报告发了出去。团是开心的,有欢迎回家的,有更多的休息,他紧张的神经得到了缓解。刚来的时候,他反复要求医生回去后再出去。医生说只要戴上口罩,基本就没事了。他担心病毒还在他的车里。“运营商在环境中生存需要多长时间?”疾控中心的人也证实了。
出院后,担心救护车会引起社会恐慌,这个群里的安抚业主丁玉玺被送到了隔离点。新闻工作者
刺耳的言论还是不断冒出来。这是一个直接的声音,“怎么了?”
有些复康者,所以“不想回家”,在湖北黄石,我会接她的社区书记场,我今年48岁。1月底住院后,密切接触者隔离政策尚未颁布,通过邻居投诉,将恋人的女儿送到隔离点。因此,字段尤其与邻居相关。
秘书在社区里很自在。“没有人愿意遇到这种情况……”天京不尴尬。圣灵很紧张。他打算加入他,用酒精喷洒黑暗。
拿回手机卡,邻居指着门。我如何能回家?多少人有一些感染者?在他们的房子之后我得走几层?
田静的刑期真的被减了,皱眉要回家了。
冬夜是孤独的。回家的第一天晚上,田静静地坐在卧室的床上,睡不着。“我不应该回来吗?”她想不通。
过了几天,邻居的谣言又出来了。
天京家住二楼,房间的窗户是空地,厨房的排气口在空中,天气在阳光下,聊天。他们的讨论声也从窗外传来,“喂,他已经撒了毒,你离他家远点。”
天京也没理会。“你怎么会呢?你只能听别人的,不是吗?”她向记者承认。
一天早上,冲突几乎升级。窗外,她看到树后的邻居正盯着她的房间。“就像关在动物园里的动物”描述了这个领域。
她没办法。她只是生气。她拿起电话拍了张照片。没想到,男子拿起口罩,对着窗户吐了一片痰。她无法停止害怕。
烦恼集中在一个小房间里。早上醒来,晚上睡觉前,想想现在的情况,又很安静,泪流满面。
邻居的健康就是她的心灵等等。大京每天问一个爱人,邻居都在干嘛?听到肯定的回答,我的心都掉下来了。“有什么事,人家肯定会往你头上套。”
谣言从社会传播到城市和网络。过去,在时,曾有人担心京州的第一个危重病人。
李振东1月31日出院,2月16日左外野有点痛,医院又复查了一次。李振东知道这是否是一种复发。他做了三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讨论。
2月19日,他的手机突然被大量信息淹没,他打开了和朋友的微信聊天截图——“因为之前在李振东复吸,现在社会成了重灾区”
新增确诊和疑似病例、社区强制隔离、住户,李振东猜测主人“有想法”,认为自己是传染源。
事实上,在初步诊断后,李振东的父母所在的社团并没有联系原来的社区居民。
这个截图是循环的声音和不同组的声音。微信好友,不知道的会发他的个人信息,打电话。
四天后,当区防控指挥部向社会公布所有病例时,李振东感到“无辜”。
很难听到他和你家人的消息。视频聊天,家里人不小心说,开始的时候不敢出门,怕鼻子尖的人觉得尴尬。
沮丧,愤怒,那一天,他总是想着这些事。后来,他不记得了。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被全网转发了。一个月后,证实荆州市机关信息综合大楼、荆州市重大突发事件疑似病例报告网有一起案件,李振东的姓名、工作单位和家庭住址被泄露。
当时他病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得个生死,电话就转到我手机上了。很多顾客问他的病情,担心你被感染。
这就是他
后来知道,而还有一些我知道的是,情人找人问人,最后我道歉,但我还是不知道哪一个有披露。他被冠以“毒王”的名字,在网上,恐慌情绪仍在倾泻,“我说,我已经感染了我们的人,后来只要我去变,每个人都感染了,李振东的同事家里没有一个人已感染。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病毒是什么。正是这种传言是真的对人体有害。”
出口和隔离
很难恢复。武汉女孩霓旌73岁的奶奶住在老社区在孝感镇,3月11日,街道书记担忧地指出,特意安排在晚上的隔离之后。我不知道怎么泄露的消息,进入封闭的社区的大门,数十人被困老人进门。
这场闹剧终于拨通“110”。警方劝无效,但他们护送霓旌奶奶到门口。
霓旌说,老太太怕触摸到邻居,然后我不想在家里开的窗口。清洗衣物时,只是不敢晾在卫生间,怕挂在阳台上跌落楼下。
作为该领域的租户,徐生的家更长时间。
父母早年来到广东,他们在村里住的房子了十余年。 1月27日,徐生被确诊为新皇冠肺炎。当天下午,救护车拉着警报上门,房东最后一段话:一个星期之内搬走。
父母打电话找到一所房子,因为家人感染了人和湖北人民的身份,发现了十几个没有水果。
“你住在那里,我们不能回来。”
徐生了解到村委会规定了所有房东,不接受湖北人民,违反罚款。他后来找到了村委会,工作人员告诉他,只要房东愿意租房,就可以打破并提供他的健康证明。
看到移动时期正在接近,于2月16日,徐胜发了一封帮助。在信中说:“我们克服了”病毒“,但它被”病毒“共享,孤立,无处。”
下午,徐生镇交易,安排了酒店住宿。镇政府与房东谈判,为房东提供了两个月。 2月25日,徐胜终于回到了房间。
回家,外出不太容易。 3月14日,湖北黄石康复的门发布并通知了社区。社区表示,他会锁定链条锁门。他无法接受它。 “我们不是囚犯,更不用说,仍然没有人们想要生活。
大多数时候,这是无意的。武汉的治疗邵盛强发现,家里的房子的眼睛有一张粉红色的纸,一个爱情圈,一系列的词语“肺炎预防和治疗”,他总是觉得有些人没有品尝。
“肺炎预防和护理家庭”的词语张贴在康复上。记者
“标准工作流程,它没有任何错误,但它带来了这种感觉。”湖北心理顾问协会秘书长,国家二级心理辅导员杜玉军曾经在心理热线手机听到“羞耻”评论。
“耻辱是在大规模的公共事件中,社会将被添加到个人的感情”,杜玉军逐渐明白,康复不仅是一种心理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回到社会
徐胜妈妈已经失去了10年。最初,它是一个延迟的老板,所有私人项目都被清除了。报告结束后,询问其他职位,老板揭示了辞职,问题,“你知道有多少人在抱怨你吗?你知道你现在是一个名人吗?”
“她当场哭了,又回家了很久”,徐生只继续说服她的母亲,内疚。当我闲暇时,我的家人坐在一起,互相安慰。 3月10日,徐胜告诉记者,母亲被镇政府谈判,母亲赢得了另一个帖子,但它只有一倍多。
徐生表示,痊愈的患者也经历了类似的困境,“他通过了两三个孤立的时期,公司仍然没有让他去,他觉得它被改变了。”
如何真正回到人群中,并担心康复和家庭。
2月18日,“浙江工人日报”报道了湖北员工在杭州食品有限公司工作,由于诊断患有新皇冠肺炎,公司决定取消劳动合同。
湖北周鹏的康复仍然在线,但已经计划在未来工作。当他坚持穿面具时,他很热,直到天气;他准备留在一个独立的办公室,使用麦克风与员工沟通;去上班,去上班,去下班迟到;订购臭氧灭菌机,“尽可能在环境中提供更多的安全性”。
湖北的杰出工作早期,经过14天的出院后,丁玉辉去了工作。刚进入办公室,我的同事很惊讶,“你怎么回去。” “你难吃你家吗?”并有一位同事。还有一个直截了当的人,“回家弥补身体,回来两天。你不能有任何东西,你有什么要做的。”有些人萎缩后面,“我特别害怕,非常非常害怕。”
丁玉溪理解,“一切都是正常的情绪。”他拿出了医生的声明,详细解释了。
说更多,戴面具,心情和呼吸,叮嘱玉汇咳嗽。同事看到了他,他感觉到整个空气“凝结”。通过面具,丁玉辉看不到他们的表情。
今日中午,我一起去了自助餐厅的同事们,谁没有叫他。有些人通过他的座位,将四处走动,我将首先遇到他。
丁玉辉咧嘴笑着,通常是同事之间的笑话。这一次,他固定在座位上,我不想再离开了。 “我不能哭,我会说我有一个孩子。”其他人有笑声,他转向了计算机文档。
丁玉辉甚至想住在山上,“最好留一个月。”
暂时控制流行病,但已经填补的恐惧和羞耻不会被消散。纪录片“SARS十年·忘记时间”记录,“我们采访3(SARS患者)家庭,每个师父都会战斗,你想喝水吗?不介意用我们自己的杯子吗?我害怕不怕SARS? “
社会氛围很困难,但心理支持可能就像在创新中痛苦的痛苦。
湖北省中医药医院董事李丽留下深刻印象,对岩石医院的康复的印象印象深刻。当我被隔绝时,后者收到了朋友的电话,我一起等待咖啡。她继续测试对手的遗嘱的旅程“(朋友们),她实际上是为了照顾我的情绪。事实上,她绝对害怕我。”
这种康复还表示,今年不会出门,不要联系外界。
“慢慢地慢慢走”,李莉告诉她。
李莉给了她分析新冠和传播的传播,让她消除疑虑。 “那么我们鼓励他们,不一定必须与他人相处,学会与自己相处。从封闭的环境中工作,必须在中间过渡,慢慢扩大,适应”,李丽丽说。
当杜玉军在热线上时,它将指导治疗,分离个人和集体和社区的响应。经验,你不能因为这种经历而否认自己。 “
在手机结束时,杜玉军将与访客讨论一项行动计划,首先调整,强调生理营养,运动,睡眠的复苏。 “这是另一个焦点,把他从心脏的核心带到所有的身心。”
幸运的是,它是常常提到的两个词。 “他们还说,通过我自己的力量,将半生命第二次放在第二次。”
这是,让杜玉军意识到他们的精神状态正是婴儿的状态。价格的成本,我们必须尊重,而不是羞耻的感觉。 “
愈合的自我怀疑
当我从医院出来时,山东滨州的康复赵薇看到了太阳,并且有一种“长期监禁的感觉。”当病房分开时,窗户无法打开,她生活在桑叶的表面,偶尔晒太阳,更多的时候,只能看雨雪。
事实排放后不太舒服。赵伟的描述“不确定性”:“我想听到一个权威,说你完全恢复,你与正常一样。这样,即使是风吹的,我不必担心。”
孤立于第10天,她的精神仍处于紧张状态,“我一直在仔细跑在钢丝绳上,我想跑,跑”。
当丁玉溪被从医院出院时,有关于康复的康复的信息。他转身阅读新闻,安慰自己,并做了六种核酸试验,如喉头拭子,肛门拭子,结果都是消极的,但他周围的人让他变得沮丧。
我姐姐告诉丁玉辉。你不是在这个时候,这个人看到你的孩子,就像看到鬼魂一样快速地跑。 “孩子们已经发现了,非常健康”,丁玉辉懒得解释。
他开始错过医院的日子,他想躺在床的安全上。
出院后,丁玉辉再次与医生再次证实,“我不是真的出院?”
医生说电梯在前面,你可以下来,我们不必送你,你可以打电话给滴水,去上班,去自助餐厅,你有八个核酸之前和之后。
但我要上课,我是一个“中毒人”的想法和在我的心里。他的耳朵变得敏感,听取了别人,认为“感染”给了同事,公司的整个植物都被隔离,不能忍受,压力变大。
当我有时间,丁玉辉去了门来测量身体,“你看到了!我只有36度5”,他对门说。即使是花朵,每天吃三次,“事实上,没有问题,我想吃。”
湖北省荣军医院旧疾病部主任张金,管理加热三个地区的新皇冠流行,在回访患者中,她发现“死亡”仍然是高频,“我有一个很不舒服,如食欲是一点点,腹泻,呼吸不顺畅,胸闷,患有原有的疾病。“
在张金制作一个解决方案之后,有患者会说,“别骗我,我会死吗?” “我一天不能这样做?”放电患者在隔离点中是腹泻。无法,吃腹泻并不好,“我知道我不会出院,我想活回来,我想接受它。”
许多康复依赖于睡眠药物来花焦虑。大多数帮助,你想要的是医生的简单句子“很好”。 “当最痛苦的时候,病人和我们相处,所以他会更好地信任,并将更好地遵守。”张金说。
“我没有这种疾病,没有办法说,别人不是注册问题,张金感觉深深地,她的同事也被感染了,”他们肯定会比普通人更清楚,但他们会还像患者一样,它非常焦虑,它非常害怕每个指标。 “
一名医生每天都要求张金。 “我的背部每天都会开始很多热,我不会燃烧。”张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可以毫无疑问,“这种疾病会改变很多人。”
这一流行病尚未结束,张金不能回家,有时躺在酒店的酒店晚上,她在思考,最重要的是什么?仍然健康。
后来,张金建立了“康复房屋”微信集团,“负责终点”,“负责终点”,并遵循后续毒品和身心恢复的恢复。
一些康复将解释每个版本的指南的诊断和治疗措施;患者被核酸检测到,只被诊断为疑似病例,内心焦虑,“他说我有这种疾病,我不是这样,我很生病。不甜蜜”;有些人在出院后想到一些问题,他们会寄出医生,张晋和集团,并希望得到各方。
张金腾想象患者焦急地等待手机。有时她会回答,另一方立即发出“谢谢”。早上7点,一名6港口感染了30岁的女病人在本集团上截图,这是一个突然在从盒子中排出4天后突然杀死的事件。女性患者提出了抗体的考试,张金觉得她可能会挣扎一晚,等待早上会发出一条消息。
医生张金与患者沟通。记者
“你想要在隔离点或家里,一个人在房间里,拿着手机,没有娱乐,眼影是在等你,现在有一位小医生不能去附近去看医院,医院正在管理新王冠。“
张金说,康复集团给出了归属区的归属感,就像一个副避孕药或后盾。患者互相排出并舒适,并表示特殊管。
3月5日,湖北省医院开设了第一个新的皇冠肺炎康复诊所,主要用于出院检疫后患者的复苏和心理评估。湖北省医院传染部副主任萧明忠告诉记者,他接受了很多焦虑的康复,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有些人来,戴帽子,穿着夹克,围绕着围巾,“严格”。
除了为指标提供专业判断之外,萧明还将告诉他们:你已经是一个健康的人或普通人,但有时有一些小问题,没有完全与你一起,但这不会影响什么。
sin
张金的手机就像一棵树洞,它已经从早晨接受了医院排放的情绪。询问最多,除了是否完全恢复,还有一个后遗症,即我什么时候可以与我的家人取得联系? “很多人都觉得是一个时间炸弹。”
最初,丁玉辉面临两个孩子在家里,这一般抬起头脸上戴着面具。这位1岁的老人伸手去拿一个面具,丁玉辉不得不隐藏。
“孩子在厕所里,我会看他,瘦,从来没有新冠肺炎?喝水和咳嗽两个,我也觉得完成,你被我感染了,我应该怎么做。”
即使在家里,那场领域的领域也没有被拍摄,并且它不会觉得空虚。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衣服扔在垃圾袋外,然后赶紧去卫生间,而情人还没有来到同样的句子。
我洗了一个淋浴,她改变了湿面膜,衣服改变了水和84,然后立即钻进了他们的房间。
我必须和家人住在一起让她的痛苦。晚餐时,情人现在正在庆祝,天静回到碗里。 “你远离我。”田静说,“嘿,不要那么紧张!”他建议,天静不要听。
好像在病房里,房间位于房间之外,该领域分为家庭污染区和清洁区域,家庭也戴着面具保护它。
厕所是门唯一的时刻,使得现场感到头疼。走出客厅,她会等到家庭离开,而不是和任何人交谈;有时水太多,家庭仍然,她不能出来。向厕所,消毒也是必要的,看着厕所里的泡沫螺旋,田野感觉松了一口气。
每天都吃一场精致的战斗。家人将在食物的门口,致通风。 。
通过这扇门,她可以看到起居室的外观。在过去,一个家庭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很高兴能说,“肯定会想到以前的生活,每个人都渴望,你觉得对吗?”
感到撤退,丁玉西到病毒研究所,参加医生和疾病控制中心,“你能帮我侦查吗?” “你想给我一个孩子吗?”
“我觉得很难”,他谈到了责任的感受。
出席医生安慰他,“你现在需要一个精神科医生,很多患者希望我依靠他们,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并且有很多患者患者。这种心理是普通的。”
当周鹏在临界包容时,他照顾他的父母被感染。疯狂是好的,最后愈合出院。
等待父母稳定,周鹏终于提起,“儿子买不起,让你受苦!只等着你回来,你的儿子照顾你。”
这位75岁的母亲听了什么都没有说,只是说一句话:“我不知道有多危险,我们都认为你不能回来”,眼泪立刻下降。
周鹏才知道,当条件最严重时,他的血氧立刻就在,然后底部很低。
从ICU花了几天,周鹏听说有护士感染了,“虽然它不一定与自己有关,但他将永远感到尴尬。”
他说,当流行病完成时,他必须返回医院。护士穿着防护服看不到脸,不知道名字,“我真的要感谢他们。”
长期创伤记忆
在2月初,湖北省心理辅导员协会的热线逐渐增加。
杜玉军告诉记者,很多人把它们放在上面,但他们没有梳理。
64岁的武汉康复沉方从来没有想过太多,她的丈夫一直在ICU 50多天,仍然试图脱掉呼吸机。医生表示,病毒,大白肺,持续高烧,引起脑梗塞,它已经是一个奇迹,后期的恢复很长。
在隔离点,沉方清每天都伤害。这不是一顿饭,她读了小说要分散注意力的注意力,累了,醒来,跟自己说话,我在谈论自己,我很担心,担心使用语音商店,我希望他醒来后可以听到它向上。
这是42年结婚的最长分离。沉方庆经常责怪自己,为什么我没有找到我不愉快的早晨。
隔壁的患者三个康复的妻子已经过去了,沉方清看着原始场景的场景,泪水干燥。这是武汉最困难的时期,在十多天内没有任何地方。 “最后,坐在大厅里并在椅子上输液并不容易。针仍然在手中,人们已经过去了。”
康复,这个名字意味着它们也是灾难的幸存者。许多心理学家更关注的是,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康复可能具有创伤性应激障碍(PTSD)。
“PTSD的发病率高于正常人群的10%。SARS,我们调查的数据约为13%。玉树(地震)是一样的,PTSD的发病率仍在过去三年中。来吧“灾害的心理援助。
唐伟介绍了一些患者和医务人员有急性压力障??碍,并“重点”将在事件发生后三个月开始,有几种症状 - 闪回,醒来,心灵会记住以前的痛苦图片;避免,不敢去类似的环境和场景;警报增加,如无法入睡,听到一点点一点动作,心脏吓坏了;
邵盛强,30岁的康复,谁生病,记得了密集病房的安静。有一天,通过病房上的玻璃窗,他看到了几名医务人员朝一张床上,床是一块非常严格的白布,医务人员用白布消毒。
他害怕,还有一种不能说的心情,“有多少人经历过这样的困难?”
在病房里,每个人都见证了,没有人说话。
他周围的人已经过去了,在病人的朋友中会有一个放松的方式。 “今天的房间包装”,“我昨天没有看过它。”
回家偶尔,邵盛强将梦想病房的场景,医务人员仍在运行,看着每位病人的重要症状。
在隔离病房中,辐射防护夹克站在保护铅板后,观察胸部射击。湃新闻图
中国中医药大学广安门医院首席医师王健,提到“重点”,一些康复人民也会产生抑郁的心理状态。
王健一直在2003年进行心理干预,后续长期支持,也参与了汶川地震的救援和2014年马来西亚坠机事件的危机干预。
在SARS流行的晚期,他坐在心理学部门,有一些患者有一些患者看到这种疾病。他们有一个SARS的历史。他们已经排放了一两个或两个月,抑郁症,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非常谦虚,“我觉得不幸的是你在这一生中如何把它呢?”
一位护士留下“PTSD”,来到王健看到近一年的治疗。她在交通工具中接触过患者,感染了病毒,“我去思考,当时如何治疗疾病,我无法放手。”
有些人也在冷眼中产生自卑感。然而,王健指出,并非所有的劣等都会发展成心理问题,灾难后,去新的生活,人们会喘着粗气,患者可以慢慢出来。
“如果您需要,您也可以找到精神科或精神科医生,评估精神状态是否达到抑郁或创伤后的应激障碍,然后采取药物,认知重建,情感指导等,王健说。
目前,唐伟和王健的问题是,当心理干预队撤退时,谁是后续心理支持?你能形成一个长期的机制吗?
唐伟提出,无论是否能够在一个城市援助一个城市机制,在退货后,精神科医生,精神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已经靠湖北停靠,然后形成一个本地心理辅导员,形成一个组织,“为一个组织长期1年 - 五年的持续,我们的后方提供了技术和信息支持。“
王健已经检查了一些高风险群体,并与他们建立了联系。 “在同龄人之后,诊所可以继续成为心理咨询”,王健通过互联网通过互联网在北京通过了互联网。
愈合后,邵盛强变得乐观和开放。他开始认为除了生死攸关,一切都是一件小事,“很多事情都必须这样做,只是尽快做到,不要等待。”
整个武汉按下暂停按钮,邵胜强的创业项目还,资金链断裂,也有几十万的差距在一个月内,员工要支付抵押贷款,一旦让他关注,但他不怕, “”爸爸再次“。
在过去,他每天工作18个小时,现在我长期以来一直睡觉,运动,读书和学习。他开始看到孩子的手工视频,在他的妻子未来的旅行时间表中列出。
回到家后,邵盛强是手机上的志愿者咨询。为了不了解新的皇冠肺炎,他将在早上的凌晨收到一个恐慌的信息。 “他们看到我在严重的病人中恢复过来。”这也给了他一种使命感,让他更好地回归生活。
许多rehabilits举起捐赠等离子体的场景。丁玉溪也捐血,“弥补了这个国家的出生。”从静脉中看到血液,丁玉辉的心“感觉很大”。
周鹏变成了敏感性,血液站反馈他的血液依从性,抗体也达到标准,两名患者使用,第二天,它已得到改善,“我听专业”。
领域仍然亮相的区域。它在家,天静正在看窗户。外面的世界现在只有一排房子。幸运的是,伴随着她和一套桂花树和家庭支持。
“春天即将到来,许多叶子发芽了。”她期待真正走出房子的那一天。
(丁玉辉,天静,倪静,徐胜,周鹏,沉方庆是着名的,“王连张也为这篇文章捐款)